
013. 附: 生命不竭的原动力 —— 探访“清教徒”企业家曾文祺
文/张哲诚
来源:《耕心之旅——明基文化的苏州传奇》( 上海辞书出版社/2003年1月出版 )
我的脑子里没有“工作”
张:我无法体会这样一种状态,就拿你去浙大演讲的一天多的行程来讲,晚上七八点钟赶到杭州,盒饭还没吃完就去演讲,直到10点多。晚上和经销商开会到二三点钟,第二天还一早8点多接受专访。紧接着赶到分公司去面试新人,一路到下午再接受采访,之后马上坐车回苏州。对你来说这是很普通的两天,在我看来却非常紧张,那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过程中是怎样一种感受,是不是也觉得很疲累?你能容忍在长期的工作历程中总是处于这种状态吗?
曾:已经很久了,已经好几年了。你有没有发现那次李耀来的时候,行程也是这样。我跟你讲,施振荣来的时候也是如此。这是一脉相传的一种精神,我传下去的那些人也是有这种精神,已经传4代了,已经习惯了。所以我这样不是异态,是常态,是一个企业文化的常态。你看看我们培养的那些人,当他们有那么多的东西想和人家分享的时候,别人帮他排行程排成这样子,你看他会不会生气?他会不会觉得怎么这么累?不会。
张:在你们整个体系里的人都可以认同,跟你们接触我也有同感,也可以理解。但是作为局外人,他们能理解吗?对于更多的工薪阶层,他们在工作时限内完成自己的工作,不也是很可取的吗?
曾:你这里有两个问题。第一,你在谈平衡的问题:工作与生活的平衡;还有,更深层的是,什么叫工作,什么叫生活。你把我跟学生的演讲,在公司开会看成是工作,而我只看作是一种知识交流。我不是在工作,我跟你聊天也不是工作,我没有把你当作是工作伙伴。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因为工作而工作,我的脑子里没有“工作”这两个字,只有穿插着不断地和别人交流知识、交换意见。所以我没有第二个问题,只有怎样平衡生活的问题。那你觉得我平衡生活怎么样?如果不行的话,我是不是早就结婚了?所以我的平衡能力还可以吧。
我的大部分休闲时间都在运动、读书、听音乐,周末也常常不去上班。然后假期又那么多:五一、十一、春节、元旦,我又要常常回台湾开会。所以我怎么会抱怨工作太多,假期太少?不会。我们的很多经销商,一个月才休两天,一休息心就发慌。你再回过头看日本人和韩国人,他们不也是很勤奋?我们要跟他们竞争,又要比他们过得轻松,这个逻辑就不对。很多人在做一些不太合逻辑的事情,而我只是在过一种合乎逻辑的生活。
早期的文化冲击
张:如果追溯到早期,你认为有哪些事情和经历对你以后的思考、工作和生活影响最大?
曾:对我影响最大的,无疑是来大陆创业,由一个人变成几百个人。其次就是加入明基,做全球的光驱产品经理,在全球跑了两年多,可以去和IBM、HP谈生意,使我有机会培养国际观,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格局的人。使我今天看到美国人、欧洲人,就像看到隔壁邻居一样。第三,再往前推两年,就是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时候,我发现,台湾人一下班就跑光了,而日本人却还在像蚂蚁一样工作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种敬业精神,学会说不要因为历史,而去仇视今天的日本人。他们工作好,态度好,我们只有小聪明而已。
然后再往前推,因为在研究所里面的悠闲岁月,使我经历了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”,所以后来选择去美国念书。我算是很幸运,有这么多的文化形态冲击过我的大脑。中国文化、西方文化、当水手时感受的水手文化、当兵的军人文化、在研究所里面的“桃花源”文化,然后在全球奔走所养成的全球观……几十年下来,每两年为一个单位,每次转折都是一次文化冲击,获得了很多文化积累,让我融入了很多不同的东西,串成了我的云游史。
张:你多次谈到文化撞击,能否具体说一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撞击?
曾:其实文化就是生活的形态。很简单,一个人一开始的脑容量是这个样子。当你经历了不同的事情,跑到一个个完全陌生的环境,就会刺激你去思考,你的脑容量会增加,你自然会往上升。其实也不能说我有很大的撞击,我的个性是属于比较温和的,不会有轰轰烈烈的感觉。很随意,不强求,顺势而为,到后来也产生了一定的力量。所以只能说,一次一次不一样的生活历炼,让我累积了很多知识。
海上生活与读书之旅
张:听说你大学“跑船”的时候,横渡过太平洋,那需要多长时间?生活会不会很单调?
曾:大概横渡过四五次吧,一次大概要10到11天。生活是有点单调,不过正好在船上养成了读书的习惯。原先是因为要高考,后来就厌倦读书了。大学前两年也不常念书,直到大二暑假实习的时候。在船上就一定要养成读书的习惯,因为跟着水手们鬼混是不行的。然后我就把船上几乎所有的藏书都看完了,教科书也看得滚瓜烂熟,后来到大四考研也就很顺利了。
张:除了读书,在海上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?
曾:在海上有一个难得的经验,让你学会一个人自己过生活。我觉得那时候很快乐,因为很好奇,很兴奋。水手生活本来是很乏味的,就是打麻将、喝酒。而我却很充实,读书、写日记。那时候也养成了我的观察习惯,享受孤独的习惯。现在我也认为,人可以孤独,不可以寂寞。孤独和寂寞不一样,孤独让你有力量,寂寞的时候,你心里只有悲伤。
张:你们有没有经过百慕大?
曾:没有直接横穿百慕大,它在离我们比较远的地方,但可以望见。当时的确很惊奇,它的上空有一块乌云,那里一直电闪雷鸣,然后就是天崩地裂般的大雷雨,感觉那里像是在世界末日,好在我们离得比较远,平安无恙。
张: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恐惧吧?
曾:没有恐惧。我这个人偶尔会感觉灵敏,但通常很不敏感。我没有大喜大悲,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怀,对什么事情都很随缘。升官不会高兴,不升官也不会悲伤,外界来的东西不会对我有多大影响。但对于内在的体验,可能感触比别人深一点。当价值点来临的时候,我就会很敏感。
正因为很随缘,所以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,好或不好,我都会因势利导,不会有什么抱怨。比如我来这边,前两三年太忙,到处跑,很凌乱,压力大,又没有了读书时间,结果后来我得了肺炎,住院15天,反而让我重拾读书的习惯,当时真是读得很高兴。
前进大陆
张:好吧,我们言归正传,你在明基做了两年光驱的产品经理以后,只做了半年的显示器,然后就决定来大陆了。你当时觉得自己累积的经验已经足够了吗?
曾:这个跟经验够不够无关。第一,机会来了,就要争取,既然大家都不想来,那我就来吧;第二,我可能是当时公司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,因为我把光驱做到当时全台湾第一名。以我的经验来看,是当时公司最合适的人选,这跟我是不是完全准备好无关。
张:从踏上大陆的那一刻起,应该说你就没有退路了,只有去面对?
曾:对,人如果有太多选择的话,反而没有力量。而我没有选择的余地,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些产品,我来这边,就只能做这些产品。所以我的命运很笃定,我的价值的呈现很笃定,就好像说,“我既然被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,就必须去创造价值”。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,我的生命力比较强,就是因为我不会选太多,也没有选择。公司已经生产这个产品了,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卖掉,卖多少跟我的能力成正比,而我不会怀疑这个目标。
张:想要在强手如林的市场上开辟一片新天地,你一直坚守的竞争策略是什么?
曾:坦白讲,我总是在找他们生意模式中存在的缺点。当你找到这个缺点,然后按照新的生意模式去做的时候,就等于不是在跟别人竞争。结果会不会超越对手,能否赢过别人,成为第一名,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重点。公司是不是一直有创意,才是重点。
张:当时能够认同大陆发展前景的台湾人,可以说寥寥无几,你是否也感觉有点冒险?
曾:其实也不叫冒险。就像《谁动了我的奶酪》这本书里所讲,我只是闻到这边有奶酪的味道,我就勇敢离开我原先的奶酪。我的心理比较没有牵挂,怀乡之心也没有那么重,我就背着包包去找新奶酪了。可是台湾还有很多人守着过去的那个奶酪,对吧?
张:你决定来大陆的思想过程是不是很简单,没有过多的斟酌?
曾:一两个星期就决定了,先后派过3个人,大家都不来,那我就说来试试。
顺势而为
张:从家电市场来看,很多新进入者往往是本着分蛋糕的心态进入这个行业,明基作为大陆IT产业的后来者,似乎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,被称作“革命性”的营销策略,是这样吗?
曾:其实我来的时候,市场到处都是竞争对手,都不是弱者。我们开始也并没有一套非常明晰的营销策略,只是说,大环境在变化,我们就思考能不能找到和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生意模式去参与竞争,与这个市场是不是拥挤和空是没有绝对关系的。比如说,我们做手机,市场也是基本饱和的,但我们还是觉得能得到机会,这是很有趣的。当你思想想对了的时候,你会发现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束缚。
所以也不见得说是“革命性”,只不过我看到,国外已经出现这个局势,两三年后,中国也会如此。你提早做,就没有对手。比如做键盘,我们不可能去走那种低成本、乱打价格战的路线,只能靠品牌。品牌的立足点,就是触感。我们的键盘在触感方面是特别设计过的,用起来很舒服。所以我们主打触感诉求。但开始并没有做市场调查,不知道能否被接受。
张:这个判断,回头去看的确没有错。但是如果这个时间段比较久,而你又将资源摆在那边,就算两三年后,你有很大的市场空间,但恐怕在前一段却误了资本积累的先机?
曾:还好。我对所有产品都一视同仁,不是在赌。你前面有五六辆车子在推,你用同样的力量,你会发现这个车子推得比较快,因为时机到了,而那个车子推得比较慢。所以有些产品很快做到第一名,有些没有。比较容易推动的,我们就主推。其实最大的资源不是预算的资源,而是时间的资源。往往我去盯哪个功能部门的时候,哪个功能部门进步就比较快,而我为什么要盯它?那就依照“八二定律”去判断,哪个投入、产出比最高,就主攻。等到它成功之后,你就发现边际效益很大。
特别是键盘,用两分力就得到了30%的市场份额。但你从30%增加到40%的时候,就得投入八分力,那我就不推了,因为还有很多产品要推。所以每次都顺势而作,推不动不硬推。一方面总部一直有新产品进来,而我们也会想出一些新的创意。比如说,把显示器演变成Q-desk 桌上系列产品来推,结果一推出就卖断货。
张:不同产品的策略转折点不同,比如DVD和17寸的CRT,当你们开始主推的时候,正是其全面走向大众化的开始。但LCD可能离市场起飞的时间还比较远,如果当时不是联想掀起了液显风暴,可能还没有这么快?
曾:对啦,应该说预期可能要两年才能起来,结果因为别人助推,一年就冲了起来。
张:但如果等两年才起来,你的压力可能就会很大,那行动会不会觉得太早?
曾:无所谓啊,反正来的时候能够领先就好了。比如说,因为大环境还没有成熟,可能PM(产品经理)我就不会调最优秀的人去做,也不会用最好的广告资源。我的时间资源、人才资源、预算资源等等公司资源的分配,是一个主管成败的关键。我不是天才,这就跟我打桥牌一样,打一步牌,所有的产品都往前推一步,这个走得比较好,我就马上再推一步,这个不行,我再看别的。那个还好推,我就再推那个,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张:自2001年底更换品牌标识之后,市场认同的速度超出了预期,业绩不但没有下滑,反而上升,最主要是什么原因?
曾:我们靠的是天时、地利与人和。过完年市场往往会缺货,因为年前的存货通常都被压低。而我们的做法正好相反,在年前增加生产,加大库存,创造天时。然后自春天开始市场从广州到北京一路复苏。地利就是我们在全国都有仓库。人和是我们能够热情拥抱“快乐科技”,确立了这个独特而明确的定位。但因为我们是做攻占城池的工作,而城池很多,战线太广,所以不可能每个产品都做第一。我们会集中资源优势,同时确保各产品均衡发展。
选人——特别看重空杯心态
张:明基向来很注重选人,那么你们在选人时主要看重什么样的特质?
曾:我们不会刻意要求聪明、成绩、专业,这些只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素质。因为我们是在全国50所重点大学中选择,所以这一点不会有多大偏差。北大、清华的学生往往头上盖着一道光环,这是我们很不欣赏的。我们特别看重的是一种具有平实心态、空杯心态、海绵心态和学徒心态的人,这些特质将决定一个人的未来成长潜力。接下来要看,这个人更在乎进步、学习,还是更在乎工作地点以及薪水,而我们要的是那种“志在四方”的人。
张:也就是说,你们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态度?
曾:是的,如果态度不对的话你什么都看不到。如果庖丁态度很浮躁,对抗牛的时候就想把它杀掉,“我是屠夫,我想杀牛”,那你就一定很辛苦,你就学不到,你的刀就要天天磨。可是你如果态度很平稳,就能够看到牛的经脉。我觉得态度强烈影响一个人的能力。一个态度不好的人,即使培养出来也不是英雄,而是枭雄或奸雄。同样的能力,有人可能拿来骗大众的钱,比如利用股市造假圈钱。骗钱的人可能比我们这群人还聪明,但是因为态度不对,导致他用聪明去伤害很多人。而我要教会所有的员工,让自己心安理得去做事。
用人——多情却总是无情
张:我有一个感觉,你们的人好像很少有被降职的?
曾:你认为我们这边不能降吗?第一,比如一个人原先做分公司主管,做完之后,回来当一个产品经理,或者说随便干一个工作算不算降?第二,什么叫升?什么叫降?在官僚体制里才有升降,在学习性组织里面没有升降。
张:或者说承担责任的大小,由承担较大的责任转为承担较小的责任?
曾:那怎么会没有?到处都是。我通过让他多换两三份工作来看他到底适合哪个工作,跟是否升降没有关系,跟他是不是能扛大一点的责任有关。如果现阶段这个位置他都扛不了,你认为我会不会让他去做?
很简单,到底是我在乎这一群人,还是在乎和我交情好的某一个人。所以,不是我这个人很冷酷,也不是我很多情。往往多情却总是无情,你怎么可以把整个集团投资在某个人身上,对不对?当你看见这群人是这么努力,你怎么可以让一个人来腐化一群人。即使你有5年汗马功劳,可是你跟不上,也可以做稍微轻一点的工作。因为你有汗马功劳,就一定要升官发财,那办不到,因为我们不是慈善机构。
昨天有个经销商问我:“你跟他们交情这么好,他们会不会没有纪律,不怕你啊?”那我就跟他讲,不会啦,因为我们先要求纪律,再讲亲近。先要求专业,再讲生活。你如果专业度不够,我跟你会觉得不能交流。开除你以后,再跟你交朋友,那是两回事。最好是你又够专业,生活上我还可以当你的导师。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不也是很亲近吗?
张:最近谈论比较多的话题,是探讨一个企业的行为是否应该价值决定一切?
曾:我觉得是这样,一个人有汗马功劳,可以获得他应得的报酬。可是你不能让他的工作超过他的能力,把他提拔到超过他能力的职位。这跟价值决定论无关,跟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好的专家、主管有关,跟一间公司能否人尽其才有关。
人生应有大格局
张:对于陈吉(通讯产品PM)的第二次离职,你当时抱什么态度?
曾:来挖陈吉的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经销商。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清华毕业的,也是属于心胸比较开阔的人,他会给你一块空间去耕耘,然后只要交出一份财务报表就好了。我开始是希望陈吉不要走,不过我还是跟他说:“如果你要去的话,除非给你一个独立的舞台,那我可以帮你去跟他们的大老板谈。但不管你怎么考虑,如果在那边碰到不顺,还可以回来,”我觉得让他出去历炼一年回来也好。结果他出去后并不如愿,反而在这边他能得到充分授权,拥有更大的舞台,所以他又回来了。
张:据说有一名员工本来做得很优秀,她后来离职留在了上海。现在的明基人还经常提起她,这个个案似乎很典型,你能分析一下吗?
曾:她是一名少有的很踏实、很积极的女生,在上海做销售代表的时候,做得很不错,所以我想调她回总部做PM。但是她坚决要留上海,宁可离职。当她离职的时候,所有和她同批进公司的人都在全国做大调动,进步都很快,而她只是一两年间学了一套拳脚工夫就下山了。她的同辈人接下来接受的是主管的训练,训练操全国大盘的经验。而她出去后进了戴尔,继续在销售代表的圈子里为业绩打拼,如今已经输给同辈人很多了。她选择了上海,而没有选择自己的进步。结果三四个月不到,她离开了戴尔,又到另一家美商公司,薪水很高,但进步的空间不大。
她常常被我提出来说这个人态度很好,可是远见还不够,所要的舞台也不会大。她的舞台在上海,明基人的舞台是全国,是世界。上海只不过是一个温柔乡、壮士冢。你以为它是一个一切都很国际化的大舞台,其实不是。
当然,大学生贪恋大都市,我不能说这是错的,我也历经过很多大都市。正因如此,所以我才说,应该更看重自己未来的方向,懂得去安身立命。况且,你如果在苏州都没有办法领略它的文化底蕴,了解苏州的深层面,你到了上海也只能是看到它表面的浮华而已。我对上海或许看得还更深刻一些。
张:从一些离开明基的员工身上,哪些方面能够看出公司对他们的影响?
曾:明基对员工而言,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,就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,到底要什么。所以他们出去往往会到那种很透明、规范的国际型企业去。如果不透明不规范的企业肯定不行,他们不愿到那种官僚体系、论资排辈很严重的企业去生存。因为他会觉得生命不应浪费在这种地方,他会去一些他们认为不错的企业,或者去创业。
张:应该也有人来挖过你吧?或者你个人有没有考虑过创业?
曾:的确也有人挖我,但我不会离开苏州。我最大的兴趣在于培养人,而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。即使让我去一家公司,给我充分授权,我想要把它盘好,也至少要5年时间,人生有多少个5年可以花?所以我根本不太可能再去创业。从这里培养人会比较快,到外面则要从头做起,可能要好几年。另外,很多人跳来跳去,都是为了更高的薪水,那我不需要。像我现在这个样子,每天都有那么多新鲜好玩的事情来让我创造价值,这个乐趣哪里能够取代呢?
张:当你培养的人被别人挖走,你会不会很难过?
曾:我当然不希望这样。但是,现在别人来挖我们的人,那是不是我也要去挖别人的人?NO!有这样一个故事,说有个人背后中了一箭,箭伤好了以后,他还一直在想,到底是谁射了我一箭?他一直想这件事,结果佛陀告诉他,你不要再受第二箭,不要被人射中你的心。背上的伤很容易痊愈,而心上的伤会影响一辈子。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来自人才培养机制,我们会一如既往培养人才,这个方向并不因为有人被挖而有所改变。况且能够成为总经理的人选,几乎都没有被挖走。
个人成长优先于公司业绩
张:除了性质本身不同以外,你带人的方式似乎与学校里面老师教学生的方式还是很不一样?很多员工都觉得你很“凶”?
曾:在学校里的老师往往是当面表扬,背后批评,在我们这里正好相反。因为中国人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别人不好。但是你不这样要求,就没有办法当总经理,他们也不能去很精准地要求别人。所谓的“凶”,不是我骂你,而是我不会让你散,不会因为这个数字说不出来,没有准备好,还能让你过关。如果要对你负责,我怎么可以让你过关,你一定要讲出答案,否则就先站着,我就这样尽量逼你会。然后我把最强的人派到分公司,让他们去带新人。我要带他们去做领导,然后他们要带新人成为专家。刚进来的员工是学徒,学徒之后就是专家,专家之后将成为导师!
张:明基的轮调政策无疑对员工的快速成长起了很大促进作用。但是在太过频繁的调动里面,似乎太过注重人才历炼的需要,而忽视了这个职位本身对于公司利润的贡献。这对公司发展是否会有一定影响,并且加重了公司人才培养的成本压力,怎么看这个问题?
曾:一方面因为李耀对我充分授权,其次我认为这是对的。我认为人的流动是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方向的,我不会把人才一直摆在一个位置上,说这样更容易出业绩,可是那个人的成长恐怕就停滞了。对于公司的这批主管,我很清楚他们现阶段的能力,未来的潜力。要真正成为总经理级的人才,还需要5到8年的培养期,这段时间他们仍然会被频繁调动。而不断轮调的结果证明,业绩还是在继续成长。
我如今的做法就是先让老人去带新人。一方面培养老人的领导能力,另一方面可以不断选出成长起来的新人,让他们不必被绑在原来的部门,而是作为整个公司的智慧财产,进行内部调动。通常的思维方式是,从我的部门培养出来的人,最好能够赶快帮我把业绩做好,而不要被调走。可是我跟各部门主管都讲好,你最好的人就是要被调动的。因为,先期成长起来的人,如果不让他调动的话,他很快会感到缺乏挑战,导致其成长趋缓,那么他可能就会离职。所以,他在你的部门表现越突出,你越要鼓励他做内部调动。
郝萍(原客服部主管)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她一开始总是抱怨我把他们优秀的人调走,后来我就不动她的人。结果一年之后,她发现自己并没有留住人才,因为有的人就跳槽了。当她意识到这点以后,就放弃了保守式、本位式的领导模式。结果,她部门的人一出来,大家就会去抢,因为口碑很好。所以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舞台,心胸和组织都很开阔。
张:你曾经提到过想建立企业的“知识地图”,它对于员工教育培养到底有什么意义?
曾:我希望能够在公司里给大家一些“知识地图”,让大家知道谁拥有哪些知识。比如说把某个人的经历编成故事,不是琼瑶小说里面的那种故事,看过后哭一哭就算了。而是能够在别人的成长过程中找到和自己相似的地方,然后遇到问题可以去请教他,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。
我常常对员工说,其实在大家身边有很多资源,公司其实就是个知识宝藏,有很多知识存在于人的头脑里面。比如制造知识、工程知识、品管知识、生产管理以及行销知识,找不到就是你自己的问题。要学会调动别人看不到的无形资源。这有点类似打太极拳,因为空气是无形的,所以一般人不会以为空气是一种力量,可是打太极拳的人就可以打到好像身边有一股气流存在。
张:从“明基大学”成立之日起,明基就成为一个特殊的“教育机构”,从学习性组织演变成教导型的组织,你之所以如此强调教导,背后的依据是什么?
曾:我发现让我做事的原动力主要还是来自内心,所以我想把激发自己原动力的方法教给我的同事,然后就不用总是盯着他们。人和动物不一样,不应该是胡萝卜和鞭子的理论。人应该是在内心里面自己产生动力,是一个永动机的概念。我自己是这样,所以我认为他们也能达到。另外,学习的精神以及把学到的东西与人分享这种领导的精神,这两种东西一定要保留住。因为你一定要透过教别人,自己才能学更多。教育如果是单向的,那一定完蛋。儒家思想讲天地君亲师,把老师的地位摆到很高,这是对的。可是到后来,老师觉得自己地位高,不接受学生的批评,就不对了。如果老师认为和学生是平等、同级的,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些知识,他教学的内容和品质一定更好。
张:张忠谋也是一个非常重视教导的企业家?你似乎也很推崇他?
曾:我很认同张忠谋的观点。他认为,企业和学校的知识来源不一样,企业的最大知识来源来自于上司对你的指导,给你的压力、任务或其他东西,当你不会的时候,他来教你,那就是量身打造;第二,你在工作当中知道你的不足,然后赶快去学习,接着马上来用,那么这个学习的能量就很大;第三来自于受训,可以学以致用。
这3句话很重要,所以你去学EMBA,也必须是今天学习的内容,明天就演练到工作中才有用,然后后天就要拿来教人,否则就不要去学,你就是要这么“吝啬”。因为只有教人才能够总结经验,回过头来才知道你学得对不对,教学相长才有提高。在做的过程中,才有新经验跑出来。另外,如果你发现这个环境里面没有人比你厉害,你就要赶快离开。
用学习性组织打破官僚
张:建立一个学习和教导型的组织,对一个企业来说最大的障碍在哪里?
曾:官僚体制是实现组织有效学习和交流的最大障碍,只要有人就有官僚。就像韦尔奇所说,即使大部分的官僚制度被干掉了,但是官僚还是会出现,因为它是人性的一部分,非常难抵抗。只要一眨眼,这个魔鬼就把你占领了。因为权利使人腐化,你有权,就可以享受资源,分配资源。所以权利是最大的春药,让人兴奋,使人腐化,而官僚体制正是属于权利建构起来的机制。所以我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要随时保持组织的学习气氛和调动气氛,也是要打破官僚体制。
官僚不是只有纵向的,横向也有。比如物流部被指责,说5点钟怎么还不发车,物流部就会说,你们怎么这么官僚,可不可以5点零1分?所以跨部门就有官僚,因为不同部门有各自的任务和利益,也就有各自的本位,本位主义本身就是官僚。纵向官僚可以用扁平式的组织把它压掉,比如GE把27层压缩到6层;横向的官僚可以靠工作轮调来解决。如果你说售后服务官僚,那你就调到那里。员工经常互调,就互相体认。然后会发现,原来的思考太片面了,没有全盘考虑。当部门都变成一个流动性组织之后,企业就倾向于成为一个无疆界组织、学习性组织、无官僚组织。
当没有官僚的障碍之后,知识就比较容易流动。如果我的观念当中,我和这个人是同级的,那么你的知识就容易流动到我身上来。如果我官大学问大,不需要听你讲什么,那你的知识怎么可能到我身上。所以流动性组织里面,随着人员流动,知识也在流动。因此,破除官僚和建立学习性组织,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
不以业绩定奖励
张:公司每年会考评,但是却不主要根据业绩而定,能否清楚地陈述一下到底如何来制定奖励制度?
曾:我们年终奖金要发平均90天的薪水,这个预算拨给部门主管,然后按照10%、30%、50%、10%的比例为原则来打分。前面10%的人最高,会发到150天的薪水,后面10%的人是0,然后中间30%的人是发100天的薪水,最后50%的人得到80天薪水。打分评级后还要开会讨论,主管要一个个解释如何评定的,大家同意,那么就通过。打分主要是看口碑,不看业绩,主管要清楚报告他做了哪些事。有人说我们没有用业绩衡量是不对的,但如果那样的话,被调去艰难地方作战的人,业绩自然就差了嘛,人也就很难调动,而我们的人很容易调动。所以很多公司卡死在这一关,因为员工的奖金与他在某个岗位或区域的业绩直接挂钩。
张:没有具体的业绩指标如何激励员工去努力提高业绩水平呢?
曾:其实我们没有给一个很明确的业绩指标,说你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等等。但我会让他们知道,必须自己去找他心中的指标。我们每两个星期都要开PM周会,那么全国各地哪里做得怎么样,一目了然,所以他自然会去和同辈们比。如果给一个硬指标,他的逻辑就会变成:市场没做好是因为市场本身不好。市场做好了,是因为自己做得好。当我摆出一个同台评比的指标,他会发现,市场再怎么不好,还是有人做得好,跟市场好坏无关。所以我不是给他一个硬指标让他跟着市场好坏走,而是给他一个软指标,让他跟着人的好坏走。
我们追求进步的理念是: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,不要去埋怨环境和市场。我们员工的压力是自己乐于承担的,因为这不是被硬压的,是他自己想要赢过别人。或者也可以去做服务型的工作,不用和别人比。像物流的团队,就没有什么指标可以评估,但他们也很快乐,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他们不是去打仗的,是去运粮,去包扎伤口的,现在客服部的口碑也越来越好。
张:明基好像一直有个想法,就是让各个部门保持相对的独立性,能够越做越大,将来成为一个个独立公司?
曾:我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个部门,将来都能变成很有竞争力的独立公司,而不是说每个部门依附于别人存在,靠别人的养分生存。这有点像庄子讲的,与其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也就是说,与其互相依赖着生存,不如根本忘记水的存在,大家优哉游哉畅游于大江大湖当中,互不依赖,这样最快乐。所以我们没有哪个人会说,哪个部门是他的下属。所以有人会自愿到售后服务部,有人会自愿到人力资源部,就是这个道理。
张:如果很多部门要独立的话,一个重要前提还是要把业绩做大?
曾:李耀和我最像的一点,是他认为自己这一辈子最大的价值,就是把业绩做大。而我认为我最大的价值是把人做多,把人的价值做大,结果还是要表现在业绩上,所以我们是殊途同归。他是认准一个巨大的业绩目标,在我看来是人越多价值越大越好。他也是具有典型企业家精神的人,每一次出差,都是5点出门。他不是故意要做给你看,而是在他内心里面,有一个声音呼唤着他,他不会违反内心的声音。而我们这里每一个人,也都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在呼唤自己,他们也都认可。创造自我的最大价值是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,他们还在学,可是他们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。至于部门是否会独立,那是自然而然,该发生就发生的事情。
竞争力来自生命力
张:有些员工感觉到,在开读书会的时候,有种灵魂被触动的感觉,你是否经常会谈及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?
曾:其实我没有去想一些很虚的东西,竞争是最现实的,这个礼拜做不好,业绩就不好。所以,我们必须把脚深深扎根在大地上,这让我们避免了那种点子大王之类、纯粹梦想家的影响。我们的竞争力来自于我们的生命力,而我们的生命力又是来自坚实的大地。
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做很简单的事,跟打桥牌一样:在对的时间,与对的人一起做对的事情。只是说,我们在培养人的时候,要兼顾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。考虑长远目标的时候,就会牵扯到价值观和文化。我们认为,人的人文素养要很稳固,企业的生命力才能长远。我可能为了短期目标而派他出去打一场仗,但我希望他的战略、战术面也要强,又要能够带部队。那么他的诚信度,他的精神、价值观、人生观就必定要很厚实。如果脱离这个环境直接谈灵魂,就会比较虚,还是实际的故事最能感动人。
大自然的规律与企业生态
张:我记得那天你在办公室里讲一句话,“我们所做的事是符合大自然规律的”,你是基于什么事情这样说的?在公司的一些核心的理念和行为当中,有哪些是让你感觉到吻合大自然的规律的?
曾:我当时正好想到关于企业生态的问题,我认为把这个做好,企业自然而然就会很强。生态学就是自然之道,如果你所做的事情能够符合大自然的规律,那就错不到哪里去了。
张:其实你们是在致力于创造一个更良性的企业生态?
曾:是的,什么东西会生生不息,有不竭的力量?那就是大自然。哲学家、艺术家都是在诠释大自然给人的感知、感触,回归到最原始还是大自然。你的所作所为应该在大自然中取得一定的验证。
大自然给人的启示太多了。春天播种,夏天锄草,秋天收获,我们经营企业也有旺季和淡季。淡季来时,就该储备粮食。每一年的五六月总是淡季啊,我就不会一直逼,生意必须要做得多好,那就违反大自然规律了。所以五六月我们就做培训工作,来应付7月的挑战,这样就符合大自然季节的更替。我的把握度、自信心来自与大自然的融合,顺势而做,顺水推舟,结果就比较好。
张:看来你从大自然中吸取了不少的营养?
曾:很简单啊,当你难过的时候,或者找一个人慰藉,吐苦水。或者喝点白酒,喝醉算了。再或者是到大自然去,听听海浪生生不息的声音,感受千万年生生不息的力量,心灵就得到启迪和震撼,重新获得力量。哪种方式比较好呢?显然,人家给你的慰藉会枯竭。白酒会让你头痛。一定是来自大自然的慰藉不会枯竭,你能从中吸取一些养分,对你就比较好。我们公司每年都会安排旅游,让大家松懈一下,到大自然中去走走,到海边、山边走走。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山水可以培育出仁者和智者。
我在向大自然的精髓学习之后,再回过头来看销售怎么做,市场怎么打,就感觉那些东西变成很肤浅很表象了。比如这里为什么会长出一棵树,其实这个不重要,那个土壤才比较重要。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树林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有土壤和气候环境。更何况一些外商,是看到树林来砍树的,然后把它栽到自己那边去。而我这里主要是培育了一片土壤,只要有土壤存在,还是会长出这样的树。而被移植的,则不一定能够成活。
清教徒精神与创业
张:对于一个企业家好坏的评价,往往是看他是否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,而我感觉到,企业家精神在你身上则表现为一种很浓厚的清教徒精神,你自己觉得呢?如何看待这种精神对于企业长远发展的价值?
曾: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其实沦为“大败局”的那些企业中,一定有相当部分,是因为内心里面没有很深的道德感。正如美国人当年开发西部的时候,遇到一大堆土地、一大堆没有法律规范到的疆界的时候,一些具有很强内心规范力量的人,诸如一些“清教徒”式的创业者,他们开疆辟土,成就了事业。而另外一批内心道德感不强的人,由于法律约束不到,文化、价值观对他们也没有很强的约束力,结果就沦为了盗匪。所以在美国那个特殊历史时期,有相当多人沦为了劫匪、盗匪。同样的道理,国内很多企业在规则不完善的开放背景下,沦为了“大败局”。
当我代表明基来大陆开拓生意的时候,如果我没有像清教徒般的道德约束力的话,我几乎想怎样做都可以。比如我可以把这个地方的经销权给你,那我收你5%的回扣,公司没有人来管我,那你可以做大,我也可以有钱赚,也没有人知道。我如果道德感很低的话,就可以这样做,就像很多在海外的中资企业一样,出事的原因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如此。然而,我根本不会做这件事情,我的任何判断、任何行为,我都要求要非常专业,非常可持续发展,整个思想的堡垒没有一个缝隙,所以我就没有走向“大败局”。
很多台湾人离家来到大陆,也类似进入一个无人管辖的西部。他们发现自己有了钱会很好用,所以肆无忌惮,导致事业败局。而我即使连老婆、女朋友都没有的情况下,也从来不会利用职权去获得这方面的便利,于公于私都没有。我认为,台资企业到这边来,要想从零开始,开出一片天地,不让任何私欲去左右专业判断,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清教徒精神,否则迟早会出问题。其实这也是一种开拓企业的精神,使我们打造出今天这样的规模。
张:你将公司环境塑造得很有家庭氛围,而且你也做了很多员工的证婚人,甚至去帮助解决公司员工家庭的问题。你既然这么有心将整个明基变成一个 “虚拟整合的大家庭”,说明您一定认同家庭的重要,那你个人呢?
曾:其实我没有那么傻,我是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至于个人问题,一方面我要求比较高。其次,我比较注重工作伦理,所以没有在公司内部考虑。而在外面,我并没有认识多少人。另外还有一个重点,我虽然蛮想结婚的,但是因为我的生活过得很充实,而且安逸快乐,也就没有很强烈念头去找一个人结婚,没有什么压力,可能我太率性,太性之所至了。比如我经常在运动、看书,每次出去,从早到晚都有人找我聊天,聊完以后他有收获我也有收获。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在工作,你认为我今天早上开会是在工作吗?其实那是游戏了,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不要工作7天,让周六、周日有很多灵感产生,然后把想到的事情写在日记里面。所以我的人生是蛮丰富的,好像没有什么刻意要去做的事情。
张:我发现明基的员工在外出差往往会很主动为公司节约,都会不自觉地秉承平实务本的精神,这种精神气质是否已经被定格下来?
曾:这就是一种创业精神,因为浪费资源的人不可能有创业精神了,他们其实是在历炼自己的创业精神。因为他们知道,只要具备这样的精神和态度,这辈子就不愁未来没着落。他们如果去浪费钱,那么浪费的实际上不是公司的钱,而是个人创业精神养成的时间。公司浪费得起,他们浪费不起,这就是背后的逻辑。
简单就是力量
张:你觉得明基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?
曾:继续按照前面的轨迹,继续培养人,让他们去历炼。这也很实际,我把人培养出来,虽然难度高,但不是说不可能嘛,对不对?这就是苏州明基要做的事,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答案都很简单?
张:越来越简单。
曾:简单就是速度,就是力量,就是自信。我不讲困难是因为我一定要这样做,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,这是我惟一的做法,没有第二个选择了。只有不停地培养人,并给他们立业,这就是我的终极目标。
张:你曾经说过希望培养100个人出来,其实按你的逻辑,这只是一个虚数,实际上并不是说一定要有多少个人,关键是要不断向理想接近,对吧?
曾:是的,哪有什么100人的限制。只不过是业绩一定会大,舞台一定会大,这是互为因果的。跟数字无关,跟时间长短都无关,只跟方向性有关。就像我们做LCD一样。你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,你只要确定了这个庄严的行旅,那么以乌龟的速度爬都无所谓,像朝圣的圣徒一步一步走得那么慢都无所谓。
我们这群人的不同
张:对于一个现代化企业来说,企业的管理体系、制度,流程的科学化、规范化,无疑是非常重要的。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信息飞速流转的社会,企业其实是在进行效率和纠错的竞争,所以都在加速自己公司内部现代化管理体系的建立。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把人情、人的主观态度、情绪对于工作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。那是否可以认为,从长久来看,随着制度的日趋完善,人的态度、情感,乃至价值观将越来越显得不重要?或者可以忽略不计?
曾:你讲的是作业效率,是整个日本民族的务虚,也是国内企业的方向性错误。因为制度很重要,我就把制度完善到取代价值观的判断和要求,把人变成一个完美的机器,这是错的。“机器”再完美都不如人重要,人最重要,领导人带很多人出来最重要,为什么?因为竞争对手变化太快了,竞争压力太大了,所以我们的人随时要能够应变。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制度,即使现在完美也不等于未来完美,所以人力资本才是最重要的资本。
应该说规章制度也是很重要,系统化的管理能够帮你减轻很多不必要的消耗。有很多辅助的机构来帮你管理,你就可以去发挥你的核心价值,把整个机器往那边开动。没有规章制度就完了,一盘散沙,所以它是方便你做更多的事情,好像一个杠杆。你有了这个杠杆,用1倍的力量就能够翘起10倍的东西。所以各式各样的系统制度都是为了降低成本,帮助你去翘。可是最重要的,还是人去翘。而这个人又是带着自己的价值判断、情感、激情和强烈进取心去做这件事情的。
如果讲到组织就只有规章制度、流程,那就等于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无机体,也就是这个杠杆。而人是有机体,由人构筑的组织也是有生命的。所以组织是由两块组成,一块就是无机的杠杆,一块就是人。我相信人是最重要的。
张:在对你漫长的采访中间,你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一个主轴,就是“人”。那你觉得明基公司这群人的状态,到底和外面的人有什么不一样?
曾:在我们公司,你可以感觉到那种成长的动量、能量很足,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平静的“校园”,平静而优美的办公区里面,其实聚集着大量的能量。我们这里有很多很有能量的人,互相交流、鼓励,一直在进步。如果能测试脑所散发出来的能量的话,这里肯定是一个苏州巨大的能量源,这些人平均脑波的活动力一定比其他地方来得高。他们其实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创意,并且充满激情和斗志,这就是我们这群人的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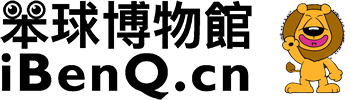
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 



